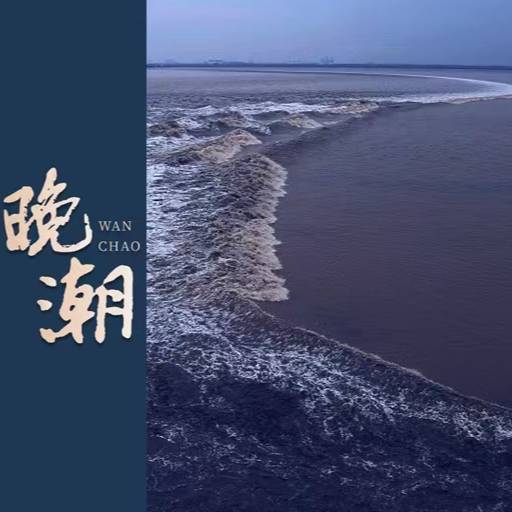钱报晚潮编辑
潮新闻“晚潮”栏目编辑
2021-06-15 13:22 浙江杭州
关注
煤球炉的记忆
□胡华军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家用的是煤球炉烧的饭菜,那个年代煤球票是定量供应的,我们家煤球票是不够用的。
我印象里煤球炉是一个圆柱形高50公分左右,口径大约在30公分圆柱形的炉子,外面包的是一层铁皮,两边一个大提耳,是拎煤球炉用的,炉子最底下横着几根粗铁丝,是镂空着的,目的是为让烧完的碎煤块掉在里面,外面有一个可以移动的小门,是为了封炉子用的。别小看这个可以移动的小门,我们都是通过它来控制煤炉的火势,它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了留下火种,第二天不要发炉子。如果你头天晚上煤炉门没封好。就会出现煤球烧尽了,煤炉灭了得重新发煤球炉,移动的小门是煤球炉火力调节的机关,炒菜时火可以大些、炖汤要用小火,这个移动的小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家煤炉,用的是煤球,或者煤饼,煤饼黑黝黝的中间排列整齐的煤孔。我们家靠煤球票是不够用的,每到月底就很紧张,烧过的煤渣的都仔细挑过,只要有点黑的煤就放在一个破脸盘里,积攒多了用冷水拌一下,用手搓成大小不一的煤球,做成一个个煤球放到太阳下晒干,还可以继续使用。
生煤炉是个技术活,生煤球炉时,先在炉底铁条上放几个没有燃烧完的煤球填底,然后,抽出一根火柴棒,擦火点上废纸,燃烧后放到炉膛内,再加上一层细柴或者一些粗柴引燃,最后加上几个鸡蛋大小乌漆墨黑的生煤球。如果发炉子你站在下风头,烟就会把你呛得眼泪鼻涕一大把。
1967年妈妈生了小妹妹后,煤炉有多了一个功能成了烘干器。当遇到天气不好,尿布干不了得烘尿布,这个活就归我了。我把煤炉的通风口关小,留一条缝,上面放着一个铁丝做的架子,把凉不干潮湿的尿布放在架子上面,不停地翻动着,人在旁边翻一不小心尿布会烘焦,一来煤饼就更紧张了,煤饼不够用怎么办?外婆使尽了浑身解数,外婆会托熟人去买点煤灰来,这都是煤饼店扫出来的煤灰,这种煤杂质多,烟也大,但总比没有好,至少家里够用了,外婆很会精打细算地用煤,烧饭菜用煤饼票买来的好煤烧,烧水就用煤灰做的煤球,这样一大家子用煤问题就解决了。
南方的冬天是阴冷的,夜间降温后,冷风习习,一到晚上煤炉便搬到里屋,封了它的通风口,放上烧水壶,这样一个煤饼缓缓地能烧上一夜,屋子里就有了温暖,天亮后,那炉子上的水壶里的热水还可以拿来刷牙洗脸,还不用发煤炉,加上一块煤饼又可以用了。
煤炉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煎药,外婆有支气管哮喘,老中医配的方子还是灵的,外婆吃了几幅药病就好了,只记得中药罐在煤炉上煎,屋子里散发着浓烈的中药味……
煤炉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淡出人们的视线,完全被煤气炉所替代,连煤渣都是好东西的煤饼店,如今失去了它的位置,红极一时的煤饼店不见了踪影。
煤炉只是一个时代出现的产品,而煤球却燃烧着自己,逐渐从脚燃烧到头,它是整个身体从黝黑慢慢到白褐色,它的生命也就跟着消亡。岁月流转,时光回眸,煤球炉,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它见证了一段历史,记录了那个岁月。在那物质生活贫乏的年月里,它曾经温暖了我们的心灵,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一把长柄铁钳,生火时发出的浓烟,暗红的煤球……
作者胡华军,1954年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1970年1月入伍浙字414部队话务员,1970年3月十二野战医院卫生员,1973年6月十二野战医院护士,1979年2月随院参加自卫反击战,1982年转业到地方供职于浙江外国语学院,2009年退休。热爱文学。作品发表在《绽放军花》《兵妈妈》《战火岁月》《追寻》《中国反击》《宿迁日报》《 印象文山》《军嫂》《 老人春秋》等报刊。著有散文集《心中的蓓蕾》。现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