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客_陆咏梅
关注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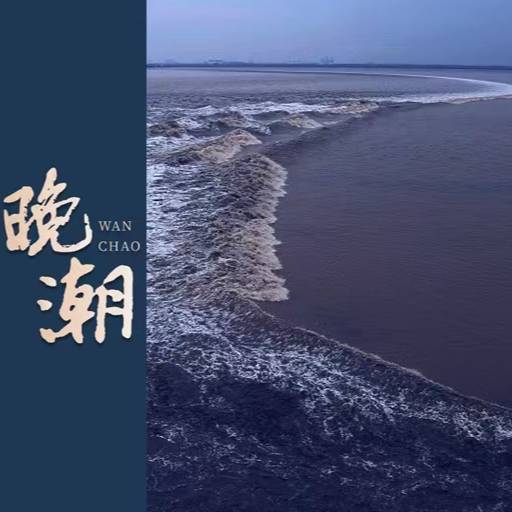
晚潮
理发与剃头
作者 陆咏梅
临近年关,想意气风发,焕然一新,要先理发。
去哪儿理发?偶尔做头发,不肯拿自己当试验品,搜到一家店,网评好,列了几种价格,价差不小,服务的差距在哪呢?
父亲卧床多日,癌细胞吞噬了他的机体和活力。他爱体面,耄耋之年,清晨起来,涂一点牙膏,一手绷紧脸皮,一手举剃刀刮脸,面目干净了才出门。气若游丝,久未理发了,开车送镇上?
母亲很坚决:“他坐不久,等两天,剃头的来了再说。”
理发店亮堂堂的,装修风格前卫,黑白两色分明,门童恭候,身子前倾,戴着口罩也遮不住从眼里流出来的笑意,服务生衣着清一色通黑,理发师着装不一。短裙姑娘抱着便签夹,热情地迎过来:“剪发还是染发?”
“剪发加烫发,350和390元,有什么不同?”
“剪发有150、120和80元的价格,不过150和120的老师已下班,现在只有80的老师。”她把我们引到咨询台前,让同事给明确答复,“150和80元没区别,剪发老师工龄有长短。”
说话间,一位长相乖巧的男孩,接过我们的包裹大衣去寄存,然后,把存包钥匙递回。
短裙姑娘将我俩安置在真皮座椅里,明净的镜子,雪白的墙,灯光明亮。
姑娘问:“喝点什么?稍等,老师来了跟你沟通发型。”
发型师身穿深蓝浅蓝交错的格子衬衣,皮肤白皙,二十出头,声音细弱但清晰:“你想要怎样的发型?有照片吗?”
他细看我提供的照片,取梳子在我头上摆弄,评估发量头型,向短裙轻声说:“安排洗头。”
凛冽的清晨,母亲说:“今天初七,剃头的会来,我先烧壶水。”
母亲烧好水,剃头的来了。剃头师傅一进门,我吓了一跳。他走街串巷五十多年,居然还背着剃头箱子云游,弟弟当年的满月头是他理的。太阳明晃晃照进门里,师傅边开剃头箱,边让母亲安置躺椅。箱子一开,荡布一挂,操起剃刀磨开了。新木箱子里的格局和四五十年前一样,许多小格子,整齐地码放着剃头刀、荡刀布、剪子、梳子和石粉。明晃晃的剃刀在荡布上来回荡磨,“嘶嘶嘶,嘶嘶嘶”,仿佛半个世纪前的画面凝固了。
母亲说:“师傅每月逢七来,初七、十七、二十七,只是你常年在外,没撞上。”师傅温和地笑笑:“你在外,没撞上。”
我和母亲搀扶父亲躺进椅子里。师傅用脸盆兑好水,用热毛巾摩挲父亲的脸和发,父亲惬意地闭上眼,像任人摆弄的婴儿。
来了一位短发姑娘,引我到洗头池边,躺进黑色皮椅,替我披一层银灰罩衣,系好腰带,领口围一圈纯白洗脸巾,取一条柔软的一次性无纺布围脖,环绕我的脖子扣好,围了块透明的一次性塑料大围兜,我的身子像裹了一层保鲜膜。“哗哗哗,哗哗哗”,姑娘放了好一会水,水温稳妥才引流到我发间。搓揉、按摩、打洗发水、清洗,反反复复,最后取纯白柔软的一次性洗脸巾,沿耳朵、鬓角、头皮,一一吸水,干干爽爽地,引导我到镜前坐下。这种种流程,温柔体贴,步步到位,给足了情绪价值。
一块白色布围兜,“哗”地抖开,围在父亲胸前。一把推子,在父亲头上耕耘,一寸一厘推,从脖颈到后脑勺到天灵盖,从两鬓到顶上,三千烦恼,一丝一丝飞落。
一把剃刀,刀背厚实,刀刃锋利,薄薄的刀口在父亲的头皮上游走,像绣花的手,针脚绵密;像雕花的刀,丝毫分明。师傅拧了一把热毛巾,覆住父亲的脸,软化皮肤和胡子。
一支短管软毛刷,沾了剃须膏,抹过父亲的下颔人中。剃落的须发在刀刃边黏腻,而后跌落地面,一撮撮,一绺绺,花白掺杂灰黑。须眉,是男人的代名词,须发徒长,是父亲生命边缘最后的电光火石。临近年关,父亲的颜面,由剃头师傅来保全,保全他最后的体面和尊严。
发型师细声细气,像个高中生,名字带韩国风,说干这行有十几年了。手拿剪刀,剪刀银亮,手持梳子,梳子细巧。他梳起一绺头发,像织布机上一排经线竖立空中,左手指夹住头发,一刀剪下,匀齐快捷。指掌间,梳子和剪刀交替,腾挪跌宕,仿佛翻手的云,覆手的雨。取一只银光发亮的圆环电吹风,风大,声小,利利索索吹走碎发;取一方素净的纸,仔细清理我眼角眉梢的碎发,心细如丝。短裙姑娘递上温开水,杯口扣一只纸杯盖,主打一个细节控。
父亲微微闭眼,师傅那些熟稔的手法,在顶上重温。岁月的操劳,往事的烦恼,大抵在这须臾的摩挲里,得以些许释放。父亲卧病在床的昏暗日子,终于有一个人,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手艺人,带来一些外界的缓冲,带来一些沉郁许久后的情绪刷新。
这个手艺人,他周而复始游走,周而复始上门服务,半个多世纪都这般游走。新的面孔不曾增加,老的顾客逐一老去,他也步入老年的行列,曾意气风发明净的脸布满了老年斑。他轻轻按压父亲光亮的头皮,摩挲父亲洁净的脸额,像母亲抚摸孩子一般轻柔,翻出长柄耳勺,替父亲采耳,父亲像乖巧的孩子,转了右脸转左脸。父亲双眼微闭,许是没气力,许是默默享受久违的惬意,他已经耗尽生命和激情,拼却意志和智慧,该完的人生事功都已完成,再无气力表达哀乐。
发型师去掉一次性围领,清除一次性洗脸巾,卸去塑料围兜,示意我上二楼:“楼梯陡,慢慢走。”他紧跟着,像忠诚的侍卫。楼上暖气足足的,熏得人误以为过了桃花三月,入了初夏。一位手臂纹身、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接待我,发型师端上茶托,茶托里一杯照例扣着杯盖的热水,一把红黄蓝绿的糖果,二块点心,向烫发师交代:“顶上用发卷,烫蓬松;两侧用发夹,只定型。”反复交代才下楼。
纹身小伙取洁白柔软的长棉条,沿我的后脖至前额绑一圈,镜子的我活像头绑红带的敢死队员。又用一次性围领、透明塑料围兜、洗脸巾,将我严严实实武装起来。他光着手,抓起一揪揪小辫子,刷上一层层烫发胶,卷成一个个发卷,扣上一根根橡皮筋,轻重快慢,行云流水,仿佛操刀千万遍的顶级厨师,火候把握分毫不差;仿佛解剖千万牛的庖丁,缓急掌控游刃有余。
剃头师傅在父亲的头颈脸额各处,扑了爽身粉,取软毛刷轻轻扫去碎发,揭去白布围兜,“唰唰”一抖,一叠,工具一收,朗声道:“好了。”
母亲递上十元钱,笑着道了谢。父亲睁开眼,舒爽地笑了。
打开加热器,开合如蝴蝶,发型师几番上楼看进展。纹身小伙轻轻解开卷发器,带我洗了头,吸干水,清清爽爽步下楼台。发型师吹吹剪剪,剪剪吹吹,直到毫发皆妥,才引到咨询台,结账买单,加微信道别。
此时,已过美发店打烊一个多小时,店内依然三春暖。
时隔一月,父亲去往另一个世界,那次理发,是他一生的最后体面。而剃头师傅依然在老家的乡村间奔走,奔走成一间流动的理发铺。弟弟的满月头是他剃的,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理发是他完成的。他的行走是一场尊严的修补,是一份行当的顽强挣扎,一段记忆的抚慰。
迎着凛冽的朔风,走出美发店,我说:“历经十道迎来送往,接受七八人服务,换用十几种一次性用品,这是现代理发行业的流水线。”
女儿说:“这就是体验感。在同一座城,开数家连锁店必须走流水线服务。但流水线有什么不好吗?上规模就必须规范,规范就必须流水作业。”
我在城市理发,父亲在乡间剃头。理发店将高价收费转化成工序复杂的流水作业,给足了情绪价值。剃头师傅,半个多世纪游走乡村,上门服务,收取微薄的手工费,散播人间温情,给了父亲人生最后的体面。

推荐群聊 · 晚潮( 357 )
2024-10-15 08:08浙江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