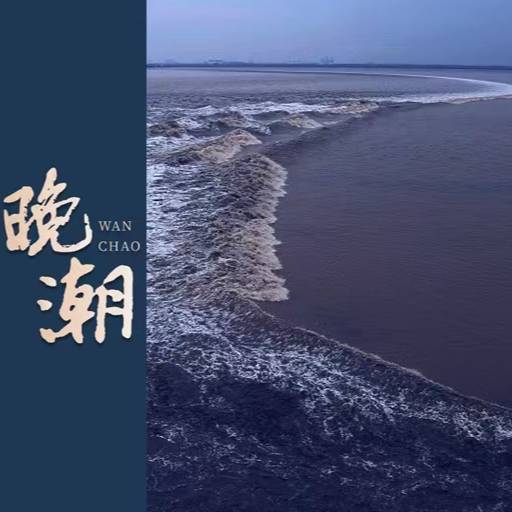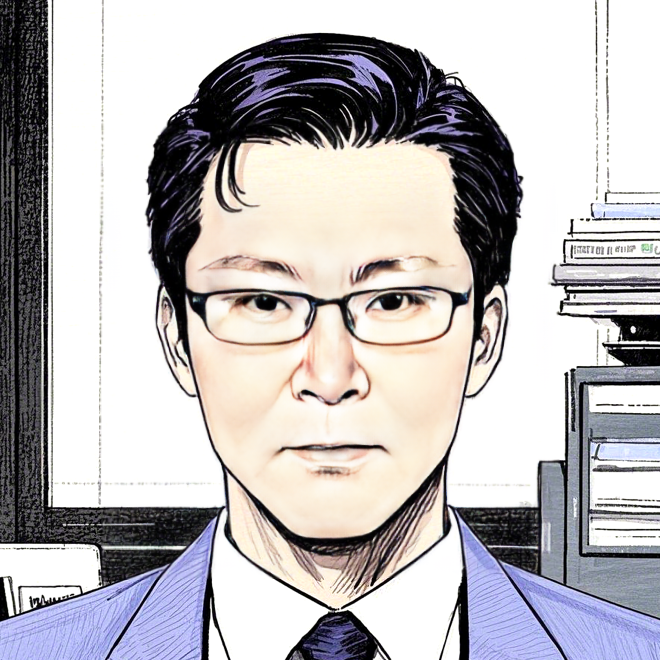
潮客_周勇
浙江森濠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2024-02-27 07:12 浙江杭州
关注
宗庆后:用读书所得去生活
周勇
“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2018年宗庆后在央视《朗读者》现场深情地朗读季羡林的《八十抒怀》。彼时,宗老已届73岁,他身着中山装,脚穿布鞋,语调和缓、深沉,眼神坚定。
从宗庆后身上,人们也读懂了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是属于读而有为的人的。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创业者,宗庆后深知读书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同时又在读书中去体会受益。
宗庆后读的书很杂,从文学作品《活着》,到武侠小说《古龙经典》,再到学术专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各种书籍应有尽有。
但是他最喜欢读的书是《毛泽东选集》。“毛泽东看历史书,主要是为了维护政权,我看历史书,是有醒悟的因素在。清朝的帝王里面,雍正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位。康熙后期,国家其实已经不行了,如果没有雍正时代前后40年对吏治的整顿,乾隆根本起不来。但历史对雍正的评价就是杀的人太多。”
他通过对《毛泽东选集》的了解,进而去思考感悟历史本身。从而形成对历史人物的独特感悟,并能客观地审视之,形成自己的判断。“我的确比较喜欢读历史书。通过读历史书,我知道了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史。历史上,中国在很多朝代都是世界强国。但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经历了近100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受尽了欺凌。历史有时很奇怪,我们当时有4亿5000万人民,却打不过八国联军的3万人。其实,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不够团结,喜欢内斗。”
在企业管理和用人方面,宗庆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过几点做法:要娃哈哈给员工最好的待遇,如在中心地段给员工盖廉租房;给自己工作过的上城区每个教师每月增加40元工资,这个措施在80年代教师每个月400元平均工资标准来看,已经是一笔不菲的补贴了。宗庆后认为一定要善待自己的员工,他说自己企业从不辞退45岁以上的员工,他们要养家糊口。他觉得人与人之间能力本来就有差距的,差一点就不要了,这是不厚道的。
宗庆后深情的朗读着:“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读着季老的文字,宗庆后仿佛在反观自己坎坷多难的人生历程……
17岁的宗庆后初中毕业后,迫于家境困窘,不得不辍学。宗庆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干起了谋生的小买卖。几年后,作为知青中的先遣人,辗转于舟山农场,绍兴茶场种茶、割稻、烧窑,海滩上挖盐,晒盐,挑盐从事体力劳动。在农村,一待就是15年。
宗庆后凭着自己的能力赢得了茶场领导的赏识,让他担任生产技术调度职务,从而有了更多时间读书。在知识的海洋中,他越来越长见识,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宗庆后所处的那个时代,也许知识没能如约改变命运,可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却是一个人走向成功、改变命运的基石和保障。
“而回头看呢,则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宗庆后读着这样的文字,获得对于成功人生的种种感悟,同样也坚定了他走出不平凡的人生的信念。
1987年,宗庆后亲手把娃哈哈“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招牌挂在了清泰街的小楼前。然而,创业之路也非一帆风顺。“人家一听是小学校办企业,就看不起你。但我们要自己看得起自己,最后要人家看得起我们。”所以,宗庆后从创业之初就提出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自强不息”的企业精神。
正是他用读书的智慧来看待生活,武装自己,才能在创业艰难的时刻,保持必胜的信心,勇敢面对眼前困难,乐观看待当下问题。哇哈哈人才走到国内饮料行业的领军地位上来。
“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对国家、对别人有益的事。”在宗庆后看来,做一些对国家、对别人有益的事是他所想要的。创造娃哈哈基业至今,他树立了民族品牌,众所周知的“达娃”之争,宗庆后在达能时任总裁扬言要让其“在法律诉讼中度过余生”的威胁之下,以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意志力绝地反击,出席了全球七十多场诉讼,最终赢得了这场持续两年半的战争。
从1999年开始,宗庆后就在娃哈哈实行全员持股。如今,已经有近2万名员工持有娃哈哈的股份。在娃哈哈工作满一年,通过考核的员工,都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娃哈哈股份,每股1元,回报率在50%—70%之间。帮助未富人群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他的理念与做法。
宗庆后的阅读经历无疑佐证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家的良知与操行。在他看来,阅读在于提升自己的视野和生活方式,将自己的阅读智慧加以运用,在生活中去检验,并能不断得到更多的启发,读书的意义在于读懂一本书,而又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益精彩!
2024年2月25日,一代儒商宗庆后辞世。他的读书故事有如他踏实、奋争,不断奉献的一生,精彩励志;他的个人魅力与光辉形象,将成为年轻一代创业者的榜样,成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