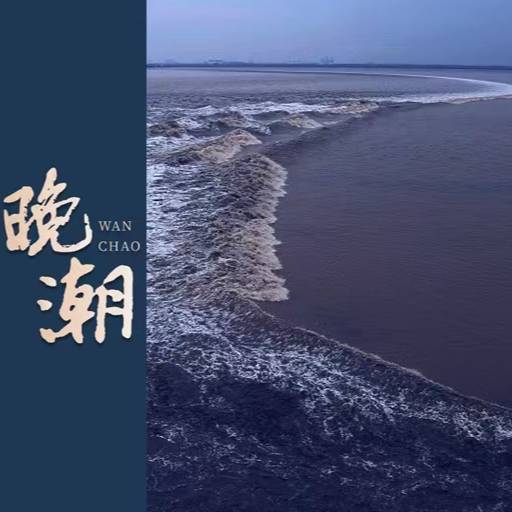潮客_竹林生鲜
静时品茶看书,也爱骑车爬山
2024-02-07 15:53 浙江杭州
关注
#晚潮#《苕溪》我的精神家园
文/朱洪祥
怀着十二分的遗憾心情,缺席2024年1月28日 《苕溪》茶花轩径山年会。这次年会是《苕溪》作者群分区分片举行的全员聚会, 也是赵焕明主编、 陈冰兰主任及杂志社众编委精心安排策划,极具亲和力的作者见面会。 通过聚会可以与此前只在线上互表仰慕的各位老师直
接见面并欢聚一堂, 彼此探讨和交流个人对文学创作的感悟和心得。 于我而言,则更是一次向众多前辈老师当面求教的绝好机会, 这样一个难得的聚会,终因工作的原因未能参加, 这也是我极想参加而又未能参加的少数高品位的风雅聚会,岂能不遗憾!
邮政一线投递员,在绝大部分人眼里, 是苦和累的象征。 我的境况也跟大多数邮政员工一样, 多年来以与过去大同的方式效劳于工作,一连几周、几月不停的忙碌, 被工作挤压得喘
不过气来,带着负担上床,又带着它起床, 把工作的忧虑变成了自己的忧虑, 努力寻找着新的路子和更简单的方法,把个人全部投入到了工作; 而情绪和烦恼常常似一条条起伏的波浪线,影响并主导我精神生活的绝大部分。后来, 一个时机的到来,心底的我,冒了出来。虽然看起来有点别扭和迟疑, 就像一个使劲想摆脱麻醉状态醒来的人, 即使他的四肢和思想还不肯完全听任于他。
曾经年少的我,由于贪玩成性,不求上进, 勉强念完高中,离大学录取分数线差了十万八
千里。不存在什么遗憾, 甚至还有点脱离苦海的味道,匆匆结束学业, 急不可耐地带着梦幻,带着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一头扎进社会的汪洋大海里,奋不顾身。 许多年来从这家公司到那家单位,从那个部门到现在的岗位。 面对纷繁复杂,叫人迷离的世界, 我青春年华的身影不停地穿梭于城市霓虹灯下的街道、 农村乡间的机耕路。在猎奇和求新鲜中, 试图把自己的外表粉饰得五颜六色,油光色亮。 然而无论外表怎样光鲜,始终掩盖不了学识少, 层次低的事实,加上草根低配的生活,而今, 在接近退休的年龄,精神上的我还是荒芜一片, 内心犹如天空中漂浮的气球,空空荡荡。 根本无需什么风雨, 只要稍稍一戳就会四分五裂,烟消云散。
正如一头在风雪中“咩咩”熬叫的离散小羊羔, 周围除了天空中肆意飘飞的满天雪花,剩下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我感觉到自己的孤单和渺小。仰望苍穹, 我内心急切的祈盼并寻找
精神的寄托和灵魂的港湾。
为了摆脱这种单薄与空洞, 我试着让自己变得充实, 一段时期以来除了工作外,绝大部分时间我把自己关进小书房里,翻翻书, 听听音乐,写一些有用没用的东西, 适当增加如骑
行,游泳之类的运动。但终究还是修养有限, 悟性不高,静不下心来,找不到精神的归处。
幸运的是,二年前, 我一篇普通的追忆已故亲人的文稿, 原本也只是当作正常的感情
抒发,试着投到《苕溪》。 未曾想到的是这粗浅的文字竟然得到了文学前辈, 德高望重的赵焕明老师关注,并给予了我细心的指导和修正, 使其发表在《苕溪》上, 甚至还被评上了好稿奖入围奖。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肯定与鼓励, 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惊喜!
与此同时,赵老师鼓励我继续写作,还把我引入到 《苕溪》作者群,邀请我到桐庐采风, 使我有机会可以向更多文学界的前辈老师学习, 我因此受益良多。正是那次桐庐采风,我见到了朴实亲和的赵焕明老师, 还有陈冰兰主任和牧林铨、董芸、 顾效迪等一大批老余杭片区
文学界前辈,并通过《苕溪》 群和临平片区的汤水根、 姚林中等老师们建立了联系。我这头失散迷途的小羊羔像找到了父母一样, 有了家的感觉。在《苕溪》作者群, 在同各位老师的交流,并在各位前辈老师的影响和指导下, 以前只是闲暇时写点小日记的我, 慢慢地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开始学习写作, 在写作中我开始认识自己,分析自己, 渐渐地有了精神上的寄托和归处。
令我收获颇丰的是,赵老师渊博的知识, 严谨的治学态度,极大的影响了我,我每一篇投到《苕溪》的文稿,赵老师都给予耐心细致的指导, 不管有没有登载到杂志上,从一段句子
到一个词组,有时甚至是一个字, 都和我一起详细探讨交流,使我获得长足的进步。 赵老师是严格的老师,又是充满了慈爱的长者和父亲, 更是我的心里标杆。
现在的我,在完成一天繁忙辛劳的工作后, 下班回到家里,除了干些必须的生活家务外,便是让自己沉浸在与群友的交流沟通和其它书海文学当中,《苕溪》 成了我理想的精神家
园,这里所有的老师都是我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