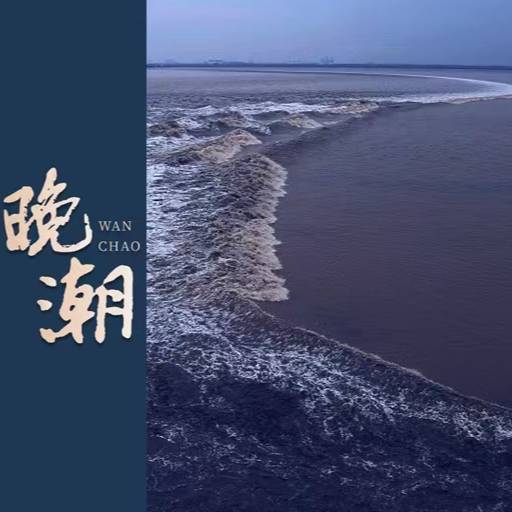孤竹小灯
人世薄凉,抱字取暖。建造师,生于燕赵,业余码字或发呆。
2023-12-20 06:40 河北衡水
关注
棉花白
关于棉花的记忆,与冷有关,与童年有关。
都快上冻了,一群穿着臃肿的人在地里摘棉花。她们围着红色或蓝色的头巾,她们身上的旧衣服颜色深重。她们从棉花地的一端向遥远的另一端缓缓地移动着,她们胸前垂下的包袱越来越鼓,她们摘着摘着就怀孕了。她们中有我的母亲,我的姑姑、婶子,还有邻家姐姐,我跟在她们后面,穿得像个棉花包。有时她们会转过身来唤我一声,送给我一朵还没有干枯的野菊花。她们拿着野菊花转身唤我的时候,她们的脸蛋红紫,带着野菊花一样卑微的灿烂,这时的她们,个个都像怀孕的母亲。有时候,不知道谁说了些什么,她们会互相推搡着,或者在对方的身上轻轻地拍打几下,像脚底下踩到蛇一样发出惊恐的尖叫,其中的某个人会咧着嘴笑起来,脸红到耳根。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棉花是甜的,纯洁的甜,每一朵棉花都是棉花糖,空气中也带着丝丝的甜味,我摘了一朵放在嘴里,绵软。而大多时候,她们都是沉默的,伴随着几声欲言又止的叹息。那些清冷的叹息夹杂着初冬的薄雾一起飘到我的耳朵里,我听到了:男人、衣服上的补丁、忍耐和妥协以及年复一年的灰白的日子。这时的棉花是温暖的,他们就像孩子一样伸出胖乎乎的洁白的小手,轻轻地安抚着那些摘棉花的人。有个人说着说着就流下了泪水,她眼前所有的棉花都齐刷刷地举起了洁白的手帕。
一晃,离开那个盛开着棉花的村庄已经很多年了。当年带我去摘棉花的姑姑婶子们都和母亲一样苍老了,她们灰白的头发飘在风中就像尘埃里的棉花。她们和我唠起家常时照样会发出几声叹息,只是她们的叹息中多了些新的内涵:天价彩礼;家里的房子再好,不在城里买房照样谈不上对象;举债结婚的,过不了几天,女方又嫌婆家债务太高说离就离;过得好好的小两口玩了几天手机就跟别人跑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等等。曾经送给我野菊花的堂姐姐,她十六岁的独子在某年夏天游泳时溺水身亡。回老家时,我带着儿子去看她,她抱住我的儿子泣不成声,嘴里不住地抽噎着:“龙龙本来都会开拖拉机帮我干活了……”如今,她和丈夫离婚了,一个人在秦皇岛打工,偶尔用手机窥探虚无飘渺的爱情。
如今,老家已经不种棉花了,清一色的玉米。以前种棉花的地种玉米,以前种麦子的地种玉米,以前种水稻的地种玉米,以前种红薯的地种玉米,把苹果树、酒葡萄砍了还种玉米。玉米省事。男人们可以省出时间到工地上拼死一样地打工。我兄弟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农民也都腐败了,没一个好好种地的。但是如果不出去打工,仅靠这点地活着,也只能拉着棍子过了。咱村那俩小超市,所有东西都可以赊着,等男人们打工回来,几乎把钱全放到那了,一年拼死拼活地在外面卖命,都是给超市打工。”
深秋,棉花白了,亘古的白。不在我的家乡白,在两百里外的芦台、塘沽白了。海边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棉花们扎堆聚在一起,伸出洁白的小手静静地等着摘棉花的人。这时打工的男人们回来了,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们去海边摘棉花打短工,这是他们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女人跟在男人的后面,孩子们跟在女人的后面,棉花们用白胖的小手不停地抚摸着他们,默默地听着他们说天气说孩子说明天。棉花的白时常让我想起一位古代的善良温婉的女子,她的手是洁白的,脸是洁白的,心是洁白的,她的灵魂也是洁白的,她把自己卖身的钱分出一部分来,给那些辛苦的摘棉花的人。2023年12月2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