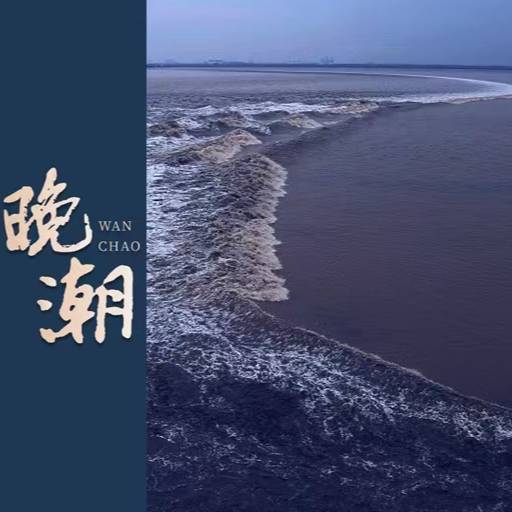潮客应爱卿
生如夏花之璀璨,死如秋叶之静美。宁波市作协会员,慈溪市作协会
2023-09-21 04:57 浙江宁波
关注
粗茶淡饭
这几天一直没有去买菜,吃的蔬菜都是送来的。小五房乾源生态农庄幼培给我送来茭白、丝瓜、夜开花、更豆、毛豆,农庄不使用农药,只使用环保酵素施肥种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好友紫燕送来的,花生、小青菜和一大袋番薯,她老爸在屋前屋后的几分地里种出来的。
这两天的菜谱是丝瓜炒蛋、夜开花炒虾皮、咸菜炒毛豆、茭白炒毛豆、清煮茭白、烤更豆,煮花生、蒸番薯、清水煮青菜。吃得很素,但是很鲜很甜。
今天的早饭是刚刚出土的番薯,番薯在高压锅蒸了一下。糯、软、香,剥开红色的皮,肉身是金灿灿的黄,香喷喷,略带甜味。昨晚上的菜是把茭白清水煮煮,酱油沾一下,清甜,美味。紫燕她带给我花生的时候,花生上的泥还是热的,出锅的花生,连汤水都是鲜的。小青菜我也是清水一煮,立马起锅,拌点猪油和酱油,直接放入口中,有点烫,吹一吹,满嘴鲜嫩和碧绿,我是狼吞虎咽把一盆小青菜卷席一空。秀色可餐,垂涎欲滴,透骨新鲜,忽然觉得这些个词专门是为此而造的。
这些菜是特别寻常的,吃着这些菜,没有惊艳,只有亲切,确实是好久没有吃到如此纯正的自种蔬菜,时间久了,便总惦记着这份亲切。
这些没有使用农药和化肥的蔬菜,叶片上都有着虫虫洞洞,丝瓜、茭白身形也细瘦不起眼,更豆的长度比大棚里的更是短小,产量当然也低了许多,只为自种的吃菜,也无需考虑产量与成本了。这些菜清淡质朴,行事低调,无须精心料理,只要拔除杂草,就任意生长。番薯、花生更是匍匐于地,埋头生长,不屑于诗词里的风雅,只在意平常日子里的烟火气。
这几天的菜看着都是普通的菜,可与菜场里的味道着实有着区别。这些蔬菜卖相虽然不及菜场里卖的,但味道就是小时候父亲种的菜,和母亲做出来的菜味非常相似。就说烤更豆,看着更豆很老,豆身矮小,还留着虫子吃过的坑坑洼洼,等烤好一品,着实比菜场那碧绿的长更豆,更柔更嫩。过些天霜降后,被霜打过的蔬鲜,如大头菜、萝卜,更是吃着又甜又糯。
小时候,秋收后,天气转冷,母亲总会做满满一大锅烤大头菜,在大头菜锅里放几段年糕,母亲的做法喜欢放暗油,就是起锅前放几勺自家打的菜籽油。放学回来,寻着香味,打开锅盖,大头菜和年糕红彤彤的,裹满菜籽油香,油光可鉴,我想没有比大头菜和年糕更好的配合了。那用稻草木柴的大灶焐透了的大头菜和年糕,酱油、菜籽油已完全渗透,我无法用文字形容那样的滋味。对着烤大头菜真的是垂涎三尺,我和哥哥是狼吞虎咽抢着吃。现在想起,不由自主口里生津。这一碗烤大头菜里,能看得见山,能望得见水,能记得住乡愁。在穷困年代里,这是根植于人灵魂深处的家乡烟火味。
种的大头菜、夜开花吃不完,便于储存,母亲还会把它们切丝晒干,过冬的时候蒸肉吃。大头菜丝、夜开花丝蒸熟后,从干瘪到丰满,肥肉溶解下来的油脂,全部被吸附,沾满油水的大头菜丝,仿佛吸入了肉的灵魂,直接下饭两碗。母亲是那种特别会持家的农村妇人,会想方设法变花样,做出不一样的菜。她还把大头菜腌制,大头菜入味了,堪比雪里蕻咸菜一样无比鲜美。做一大锅大头菜汤,快起锅时放几只蛤蜊,是相当下饭的。当然用它煎两条青占鱼,那是待客之菜了。这些时令蔬鲜,风味多变,常吃常新,常吃常想,其味至上,无与伦比,万般滋味唇齿间。每一种滋味都以人间烟火抵达了生活的清欢,每一种滋味都以日月精华诠释着岁月醇厚。
现在物质丰富了,在“有鱼有肉,喝点小酒”已是常态的日子里,鱼虾肉不断,人长胖了,嘴巴吃刁钻了。但随着年长,我好像越来越喜欢吃粗茶淡饭了。
我的居所附近,有一大片荷田,是一对安徽夫妻租种的。每每散步路过,水面上长满莲荷,见荷叶硕大,随风摇曳。这些天看见租客在采摘莲藕了。田埂上扔着许多采断的莲藕,那对租客夫妻说,如果不嫌弃,拿几节回家炒着吃。心里想着他们扔掉也是可惜,就拿回家做菜。母亲做成炒糖醋藕丝,藕丝爽脆,有嚼劲,酸酸甜甜。还放了些青椒、红椒细丝搭配,色泽亮丽,还有一股漫散的清香。颜值和口味均是上乘。妙处还在于下饭,我吃了一大碗米饭,哎,我的减肥计划又成泡影。
又到了秋收的季节,什么季节吃什么菜,我还是喜欢旧时味。八月黄等着采,芋艿、番薯、花生、萝卜……它们虽然卑微,它们却连接着乡愁的土地,在味蕾记忆里,满是它们的清甜,脆生生的味道。
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