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蝉鸣半夏
每逢夏季,耳畔最不缺的,大概就是高亢的蝉鸣。一开始,我亦嫌弃它的聒噪,可渐渐听懂了蝉的心籁后,才愈觉其中盈溢动情婉转之妙。清脆悠长的“知了,知了”,不仅在宣告它的夏日主权,于佛家看来,亦可谓禅的蝉,更会如诗般清扬鸣唱,以致让人的性灵臻于空灵澄明的化境。
初唐时期的虞世南,曾写下一首咏蝉的千古佳作——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通过以上对蝉细致入微的描述,我可以想见这样的画面:蝉独自栖在高高的树桠间,每日低垂着触须,轻盈啜饮清凉的甘露。那清脆悦耳的长鸣声,有如淙淙的流泉从萧疏的梧桐树上传出。因居于高处,故而声自远扬,并非凭借吹拂过境的阵阵秋风。
经历过隋初和隋末战争的虞世南,面对烽火狼烟里的亲人离世,也曾孤苦无依,失去所有家族地位及财富。可他自幼学而不厌且胸怀大志,又岂肯屈从命运的摆布。直到63岁那年,终于位列大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性情刚烈,直言敢谏,深得李世民敬重。太宗赋予他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虞世南才华出众,人品如蝉,一生不向权贵妥协,81岁寿终正寝,陪葬昭陵,赐谥“文懿”。“居高声自远”的清贵背后,是不凭藉外力,自能声名远播的风度气韵和耿介自信。
诗人以蝉自喻,亦是自勉自励。虞氏强调,修养成完美的人,其实不需要过多地借助外因,他的名声就会远播千里,受到人们的爱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诗人赞颂的正是植根于人心灵深处那种内在的品格和人格力量。读完该诗,我们不难想象诗人自身的清廉纯正、雍容不疲。
继虞世南之后,因为得罪武则天而被诬下狱的骆宾王作出了《在狱咏蝉》——西路蝉声唱,南冠客思侵。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身陷囹圄的作者借物言情以蝉比兴,用“露重风多”比作自己所处的环境,用“飞难进”和“响易沉”比喻自己此时的艰难现状——露重翅轻,无法高飞;风多风大,声被隐没。此诗作于患难之中,寓情于物,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抒发心怀高洁却不被人相信,满腹心事竟无处表诉的怅恨之情;同时体现出骆宾王自身不亢不卑的性格,无论如何蒙难,纯洁无瑕的报国之心兀自坦荡清白,亦表达了对黑暗世道的控诉和不满。
光阴流转,时间来到了晚唐时期。生于乱世的李商隐虽然才华盖世,却壮志难酬。当时的政坛上“牛李”两派党争十分严重,他既为牛党要人令狐楚的门下,又是李党骨干王茂原的女婿。他在两党的狭缝中生存,受尽两边的排挤打压,一生贫困潦倒,46岁便抑郁而终。
李商隐以蝉自况,该诗表达了他虽仕途不顺,却坚守节操的高尚品性——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这首诗的译文为:你栖息在树的高枝,餐风饮露,本就难以饱腹,何必哀婉地发出恨怨之声?官职卑微,四处飘泊,而故乡的田园却已荒芜。烦请你用鸣叫之声给我敲响警钟,我的家境同样贫寒而又凄清……
正如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屈原列传》亦有言: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同样赞颂了蝉不染烟火的志行美德。太史公笔下的屈子,如金蝉脱壳自动远离了污秽环境,以便超脱世俗之外,出淤泥而不染,由此可见,蝉也算是中国儒家士子理想人格的写照。
这三首唐代最为著名的咏蝉诗,都是以蝉比兴寄托,但由于诗人的人生际遇不同,故呈现出了别样的气象风貌与人生境界。清人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这样评价过: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
而在微渺如尘的我眼中,蝉的形象又有差别,更多的还是纵使沦落命运的至暗时刻,依旧守望光明、静待蜕变的坚韧不拔。经由重重磨难而涅槃重生的飞蝉,此刻正在响震天地地歌咏着生命之绝唱!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哪怕平庸如你我,也一样能为自己盛大加冕金色的辉煌!就算只拥有绚烂夏花般短暂的人生,依旧可以谱曲出荡气回肠、震撼心魄的生命乐章!此生修行路漫漫,总有苦与泪掺半,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去对待,一颗心不因外物而凝滞,一个人不为困厄所屈服!
当故事陈酿,
一切已悄然发酵。
深埋泥土的年月日,
挣扎存活;
只为他朝,
突围命运守望花开。
蝉鸣半夏,
乃入世远去的一生。
放歌缺月疏桐,
孑然背影铿锵。
从青春至皱纹,
不过转瞬即逝。
它很小,
却从不意味无法闪耀。
唯有黑暗,
才能鲜亮光之存在。
定格永恒,
心籁在熏风里完满。
非神话,
仅普通人的绽放传奇。
“转载请注明出处”
陈骥

 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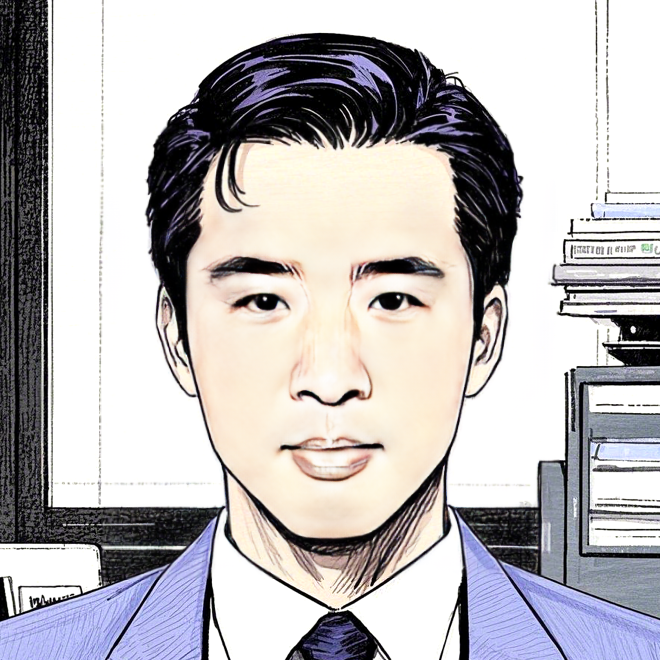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