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视窗9丨放排东阳江
水因山转,山随水处。
“放排喽!”西溪对岸悠悠传来一声嘹亮的吆喝,但见十里长溪,木排连着木排,后浪涌着前浪,浩浩荡荡,奔腾而去……
现如今,这放排的壮景,伴着撑排人的豪情,也伴着他们的辛酸,去而不返……
一
婺江,发轫于磐安玉山的“龙鸟尖”,山泉淙淙,溪流潺潺,跌瀑湍湍,清流碧潭,蜿蜒180.1公里。
磐安山水,既秀且壮,拥有七条水系,乃“四江(钱塘江、灵江、瓯江、曹娥江)之源”。东阳江是婺江的主流,磐安西溪和义乌江,统称东阳江。
山与山之间,都有缝,老家潘庄叫作“坑”。窈川,是西溪流域的一个普通山村,与婺江之源仅一箭之遥。世世代代,他们都在缝里休养生息,瓜瓞延绵。
“窈”,幽深繁茂,可组成窈杳、窈纠、窈悠、窈黑、窈蔚等等词语。川,原本指的是河流,用它替代两山之间的“缝”,似乎有些托大,但一旦冠以“窈”字,便诗意盈盈。贞远十七年(801),唐进士郑瑞隐居磐安,一日途经西溪,但见眼前“林壑幽邃,山水融结,草木畅茂”,遂起名“窈川”。
墨林,居窈川上游,是磐安的另一村庄。墨,一般用作名词,而墨林之“墨”,却是形容词——茂林修篁,色如浓墨。
大山养育了十几万子民,却没有给窈川、墨林等地的山民带来富足的生活。或者说,大山自有大山的宝藏,更多的是人们还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宝藏。大山的宝藏就是连绵不断的大山和大山上的取之不竭的林木。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山风凌冽,吹落了树梢上的黄叶。几个壮汉,玄衣打扮,腰间别了斧锯,行走在大山深处,东瞅瞅西瞧瞧……一阵接一阵斫砍之后,那些分属于不同山头的圆木都以滑行的方式被溜到了同一个地方,像赶一群没有灵魂的牲口。
山脚下的溪流边是它们的汇集地,也是它们启程的地方,至于要去哪儿,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进山的路,除了山里人的两只脚,再也盛不下别的东西,溪水成了这些圆木走出深山的唯一通道。
《小竹排》泰格 摄于安地水库
之所以称这些树为圆木,是因为它们没有冠,没有根,也没有枝桠。被修整得圆乎乎、白净净的木头,不叫圆木又能叫什么呢?当然还可以叫木材。
时间是有限制的,那得是一年里雨水最多的季节,最早要过四月,最迟不超六月。在四月和六月间,有一段梅雨季节,溪流变得不再温顺,不再潺潺,而像一头凶猛的野兽,咆哮着奔向远方。那个远方是大海,每一滴水都渴望到达的地方。正是水流的渴望和动力,也使得圆木借力变现成了可能。
久而久之,这一漂流运输的职业,便成了360行中的一行——放排,俗称“撑排”。那些玄衣壮汉,可能来自磐安的史姆、潘庄,也可能来自东阳湖溪、马宅,甚至更远的义乌、婺城等地。反正,他们有个统一称呼:排工。
1991年4月16日,《金华日报》首次组织开展“婺江行”大型采访活动。那时,我尚在磐安广播站编辑“豆腐干”,有幸参与启动仪式,并被编入第一采访组,协助陈兆斌、俞平、黄一钢完成西溪流域的行走任务。
次日,我们在尚湖镇岭西村,听90高龄的陈维庆老人述说60年前的放排往事。陈维庆满口玉山方言,语速不快,听来却有些吃力,好在有我在旁“翻译”,语言障碍得以解决,但一说到放排的专用工具,便犯难了,只能打着手势比划。
采访结束,一脸络腮胡的一钢悄悄问我:你对放排怎么这么熟悉?他哪里知道,我爸年轻时也曾放排为生,家中还留存着整套漂运用具。
我爸叫潘光品(1924.3—2013.4), 13岁跟排学艺,15岁独自撑运,直至1959年年底横锦水库大坝合龙,他才穿衣上岸,前前后后撑了二十年。
2011年国庆节,老爸因病卧床已有半年之久,我趁假期回家探望,聊起他那一代人浪头谋食的青春岁月,仿佛就在昨天。
人到晚年,繁杂的往事多已被岁月湮灭,而那些在脑海中始终鲜活如初的记忆,必定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珍藏。
二
放排源于何时,未有确考。据我老爸推测,大概始于明末清初。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春末夏初的东阳江迎来放排的黄金时期。
放排有3个环节:编排、撑排和拆排。
编排,俗称扎排。扎排,忌用普通绳索。最原始的,是一种叫檵木的槁条,手指头粗,韧性好,又抗拉。春节一过,放排人家就要上山砍回一捆捆檵木条,再借助一种类似“曲棍球”球杆的工具,将槁条扭成麻花状的藤索,信手可用。
不过,它毕竟是木本,远不是岩石的对手,一旦触礁断裂就容易散排。渐渐地,槁条就被篾缆所替代。
篾缆用新劈的篾丝绞合而成,坚韧无比。若能涮几遍黄亮的桐油,其韧度堪比用现代缆绳,即便丢弃野外,任凭风吹雨打十年八载,要想弄断,还得举起利斧。
有了槁条或篾缆的加持,即可寻一处僻静水面,把一根根待运圆木凑合起来,扎成一节节平实的木排。
《运竹人》 丹 摄
扎,不是胡乱捆绑。先要把最直最粗的上好圆木用锚固定,再挑大小、长短相近的木头七八根,大头朝前小头朝后,一一并弄。粗的一端钉上“钉钮”,槁条或篾缆窜过“钉钮”上的圆形铁环,再将它们紧紧地绞缠,然后将一节节木排首尾相连,拼接成长长的木排。
扎排是一项绝活,不下几年苦功是学不会的。而手中的竹篙,粗细适中,长约四五米,根部镶嵌着铁制的独角护头——撑排钩。
一杆在手,既可掌握漂流方向,又可避开与暗礁、山体撞击所带来的危险,更可用作扁担,晃悠悠地挑回孩子们的快乐和一家人的温饱。
木排一般扎至一米五到二米宽,一个人最多能撑3至5节。木排的层厚,由材质决定,粗大的松木、杉木只平扎一层,碗口大小扎二至三层,竹排可叠放三至四层。因为松木杉木比重大,吃水深,而毛竹空心,比重小,自浮性好。
撑排是刀口舔食的营生,规矩多,禁忌也不少。譬如,禁止女子上排;哪天开排,要翻翻老皇历,择个黄道吉日,避开农历初五、十四和二十五;忌讲洗筷子之类的话语。开排之前,同行者还要点烛焚香,拜水祭天,歃血为盟。
三
下雨了,雨量虽说不大,但接连落它三四天,汤汤雨水不经意间注满了河床。平时碧波如镜、隽秀如画的西溪此刻变了模样,像怒狮一样桀骜不驯。
塘坑口是西溪放排的起始地,目的地有东阳茜畴、义乌佛堂和金华小码头,最远的直达杭州拱辰桥码头。来回一趟,近的三五天,远的起码要半个月。
“会水的水上死,耍刀的刀上亡。”西溪流域有“三多”:险滩、“吊坎”(落差较大的瀑布)和礁石,稍有懈怠,便会引发排散人亡的悲剧。而在放排的一个个日出日落中,要经历多少危险,多少磨难,流淌多少汗水,非亲历者难以想象。让人感佩的是,即便如此,排工这份职业却从来没有因为少人干而停止过。困顿岁月,生存往往要向死亡索要。
雷滾口,两山夹一川,狭长幽深,陡峭的岩壁如同刀削,“吊坑”伴着深潭,一个连着一个。即便是山枯水瘦的冬日,墨绿色潭水深不见底,阴森恐怖。一到汛期,粗粗白练穿岩击石,飞珠溅玉,訇然之声如同滚雷,震耳欲聋。
撑到雷滾口,谙熟地形的排工都会抛甩撑杆,紧紧钩住岸边藤条,脱兔一般用力跳离排面,再攀着峭壁上的羊肠小道,快步来到下游,等待自行漂流的木排。要是错过跳离的时机,就会身陷峡谷绝境,溺水身亡。
上世纪90年代初,磐安动工兴建姜山头电站,坝址就在雷滾口最窄处。高峡出平湖,百来米长的峡谷,被硬生生地一分为二——没在库底的,难见天日;裸在坝尾的,断流缺水,苍白无助。前来垂钓者,望着那波浪不兴的水面,除了念想曾经的生态环境,还会时不时地聊起那十几个不慎葬身水底的排工。此乃后话。
东阳江全长160多公里,一出义乌地界,便遇着了源于千丈岩的武义江,双江汇合,犹如久不谋面的兄弟,终于见着,打个招呼,你拥我抱,难舍难分,以至河床像潜龙打滚似的甩尾,甩出一个天苍苍野茫茫的五百滩。
与西溪相比,婺江貌似失却了脾气,但静水深流,暗藏玄机。排工们一路闯滩过峡,早已精疲力竭,来到双江口,懈怠之心渐显,加之篾缆磨损破败,马失前蹄,悔之晚焉。
有一回,我爸要把3节100根杉木撑往杭州,忽然撞上五百滩的暗礁,首节30根圆木全散了架。幸亏那时年轻,反应也快,一瞧苗头不对,手中竹篙一起一落,犹如撑杆跳高一般跳到第二节,再举起竹篙往右侧一点,后两节木排便听话似的向岸边靠拢……无奈之下,他只能请同行村民帮忙照看,自己又“咚”的一声跳入水中,一路追到兰溪三江口,才将那些杉木一一打捞上岸。
四
十年树木,集木成林。伐木撑排,多为有计划的间伐。“窈川不窈,墨林无林”,那是后来的事了。至于原因,你懂的,无须赘述。
世移事易,岁月静美。水上漂流,是当下受人追捧的文旅项目,仅短短的西溪流域就不止一两处,票价不菲。而且,单单静水漂流,怕是聚集不了人气,还要依山就势,设置一两条拐来弯去的人工陡坡,玩得皮筏中的俊男靓女像过山车一般惊叫连连,这才惊险刺激。
命运的抗争,是祸也是福。坎坷与困境带给人的,永远是思考人生、追求圆满的机会。
(作者系中共金华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金华市作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散文学会副会长)
【后记】习总书记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八婺大地,发展迅速,万象纷呈,该如何解读,该有怎样的视野。我们和金华市社科联一起,为你打造一份权威的金华社科读本。每周四推出,帮你解开现象的迷雾,助你追寻理论的真谛。

 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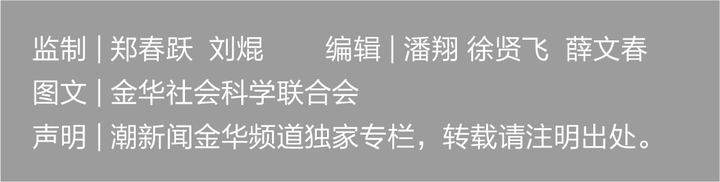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