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风物|“枫桥经验”家喻户晓 告诉你枫桥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编者按:
古越遗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会稽山顶一棵松,鉴湖水网一滴泉,千年古城一片瓦,江南水乡一座桥,还有一位位名留青史的风流人物,一个个流传千年的历史典故……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绍兴,每一寸城市肌理,每一处细枝末节,都可能蕴藏着悠久而又传奇的历史故事。
品味地理人文,解读风土人情,让历史文脉沿着时间的长河缓缓流淌,润泽人心。这是历史文明名城绍兴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也是传承宝贵遗产,打造文化高地的重要途径。
即日起,浙报集团绍兴分社重磅推出融媒体专栏《越风物》,邀请文化名家、民俗专家、文脉守护者、非遗传承人等一起讲述绍兴的人文地理故事,在感受璀璨文化无限魅力的同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强大的“文化自信”。
一九九二年前的枫桥,有枫桥区及其下属十五个乡镇之一的枫桥镇。是年“撤扩并”,新设立的枫桥镇拥纳了新枫、栎江、永宁三乡;东一迎入东三;乐山并入齐东乡(四年后改为全堂镇)。九年后,东一、全堂并入枫桥镇。今日之枫桥,区域面积在市内仅次于东白湖、店口。
以其地之广,以其史之久,以其文之盛,如果仍用东和说桥、赵家说墓的方式,是不能承其厚的。
枫桥再大,也还是会稽山支脉环抱着的一个盆地。其东北,以古博岭与山阴(今柯桥区兰亭镇)为界。其东,分别以枫(桥)谷(来)线上的杜家岭(菩提村口)与赵家镇、新(店湾)王(家宅)线上的木瓜岭与东和乡为界。其南,以绍(兴)大(唐)线上的新店湾岭与浣东街道为界。
海纳百川,而川纳百溪。通常,河流的上中游像是个收集系统,九九归一;而到了中下游平缓地带,会出现分叉。浦阳江不就在茅渚埠分为东西两江?枫桥江也在铁石堰处分出一条枫溪来。山水志载:“至镇分为二派,穿市东为枫溪,桥因以名。穿市西为五显桥。”后来,我们干过许多移位改道、裁弯截直的活。那时候,信奉“水往低处流”的朴质道理,河道就是大自然自身的选择,人可以为之让道。跟整个浦阳江水系一样,上游“地势高仰,无陂池大泽以蓄水,溪涧直泻”,旱季容易干涸见底,雨季却常常行洪不及,泛滥肆虐。所谓水利,当时主要指灌溉,能做的,就是筑堰截水。
枫桥江原本并非深广如今,那是经过多次拓宽、疏浚的。清末知县沈宝青就曾接受枫桥乡绅陈遹声之请,“以工代赈,浚枫桥江”。民国间作过拓阔,其中部分资金还是陈遹声之子陈季侃凭着自己曾任甘肃省长的声望,争取到的联合国救灾款。我讲这个,是想说,山水志里的枫溪并非我们这一代人见到的流过“枫桥头”、廿板桥,穿越在陈楼家之间的那条小溪流!
枫溪一名东溪,与作为地名的东溪(乡)各有所指。怎么确定它的位置?山水志是这么梳理的:娄坞桥溪与黄檀溪在大竹园(今仍其名)汇合后,为枫桥江;流经紫薇山,东麓有东化城寺、山巅有东化城寺塔、北隅有见大亭(即今小天竺)后,始有“东溪,即枫桥江分支,从铁石堰上北入东溪桥”。东溪“北流经枫桥市东,出枫桥”。回到山水志,“桥左为枫桥东市,去桥数丈为铺前街。路北为宋义安县旧治”,旁边的紫阳精舍,即朱熹与杨文修“谈名理处”。如此,后人所谓“枫桥头”,就是古枫桥旧址,与近年新建的枫桥江上的“枫桥”是两码事。
想象一下,以市镇为核心的枫桥区域,是否就似枫桥江、东溪托举的一艘航船?而紫薇山上的东化城寺塔、下汇地牛头山上的永枫塔,便如双桅。很难说那时有系统的规划理念,但主事者,或是地方官员,或是乡绅贤达,往往会有朴素的构想,并对这种构想抱有神圣感,持之以恒地去实践。
枫桥人都知道这两句话,“上枫桥,下柯桥”,“枫桥千根扁担,柯桥千支竹篙”。其实,柯桥何尝没有扁担,枫桥何尝没有竹篙?《枫桥史志》即谓,古枫桥下“为枫溪江航运起点”。
枫桥南望会稽山群峰,北枕古泌湖遗迹。之所以称遗迹,是因为以枫桥江为界的东西泌湖,早已不再是潴水之所,而成了湖畈,或者说产粮之地。县志《名宦志》曰,林富春“嘉靖三十四年令诸暨”,当时县城城墙坍圮,又有倭寇为患,可是公帑告虚,怎么办?“请卖官泌湖”!既然不再是官湖,《水利志》亦载,“遂无容水之区”,几家大姓“倡议合筑西泌湖埂,规私利而阖邑之水患益亟”。诸暨之湖,七十有二,大抵如此。就像后来的发展,耕地非农化在很长时间里成了趋势。《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载,“泌湖等陂泽,皆弃而不蓄。每大水后,多布网田间取鱼”,真是田不田、湖不湖。换个角度看,随着人口剧烈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才会有“天下”指望诸暨湖田熟。
正因为枫桥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它必然成为重要的商埠。一个简单的事实,香榧产区其实范围很小,也就原东溪乡境内。即使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产出,但品质没法与之相比。但名扬四方的,却是“枫桥香榧”。须知,那个时候并没有“枫桥区”这个行政区域、地理概念。《枫桥史志》谓镇上的“北春阳”、“骆恒兴”、“致和碗店”三家商号,创制了独特的工艺,用白炭烘香榧,清香可口,远销京津沪杭。一句话,来到枫桥镇上,香榧才有品牌支撑,有销售渠道,有市场空间。人称“都市诗人”的张岱,其《陶庵梦忆 》卷四 “杨神庙台阁”是这样记录的:“四方来观者数十万人。市枫桥下,亦摊亦篷。”
今天我们讲城镇梯度发展,昔日枫桥自身如果没有一定规模,怕是成不了山湖之间的中转之地。《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载:“乡镇商业之盛,首推枫桥、草塔,绍兴、嵊县及本邑纸类,皆聚于枫桥;榧栗等山货,亦以枫桥为归。”
我们接着讲枫桥东市,它止于何处?三里店。山水志谓,“旧枫桥市自海觉寺(今称海角寺)至此,长三里,故名”。位于哪里?紫阳宫(学勉中学旧址)东面“半里余,为一苇庵,俗称三里店”。
那么西市呢?得从五显桥讲起。枫桥江在铁石堰分派后,“穿市西为五显桥”,它“与枫桥并称雄要”。而“桥右为枫桥西市,长半里许,俗称桥上街。街西有海觉禅寺”。
东西两市是贯通的,两桥之间就是中市,杨相公庙(即今枫桥大庙)之所在。虽如此,却因出五显桥以西通往诸暨县城,故称“县大路”;出枫桥头以东通往绍兴府,故称“府大路”。枫桥是当之无愧的诸、绍要驿。
此外,枫桥还有南市,“名大部弄”,今青年街及至枫桥江东折一带都是;有北市,“名新街”(今仍其名)。东西市、南北市交叉处,就是十字街口。
光有这样的外部条件还不够。既然是市镇,就得有一定的公共基础设施。县府连城墙垮塌都没钱葺修,哪来的钱帮你搞市镇建设?这就得有当地世家大族来支撑,而枫桥有这个实力和风尚。别的不说,五显桥,原为三义桥,“明嘉靖间里人陈元璧、楼浚、骆珖建”,正好代表了三个大家族;而“同治年间圮”,捐修者是里人陈烈新(陈遹声父)。包括骆问礼父骆骖的别墅见大亭,“咸丰辛酉毁于兵”,也是陈烈新重建,我的理解,那个时候的见大亭,已不再是私家花园,而成了市镇客厅,当时名人纷至沓来,并留下诗文墨痕。东溪所经之廿板桥,“道光年间里人陈邦甸捐修”。枫桥江五显桥以下有大虹桥,“光绪戊寅枫桥人陈芳宝募捐”。杨相公庙后有“拯婴局,里人陈殿荣(陈烈新生父)捐建”。紫阳精舍旁有关侯庙,“庙东有育婴堂,光绪十二年里人陈垠建”。陈垠者,字步云,除建育婴堂外,还以一己之力,“筑枫桥至古博岭石路四十里”(见县志《附卷三十四·阙访》)。枫桥镇东有青龙堰,“明初枫桥人陈奫筑。康熙二十三年陈曰登重建”。
今天我们也讲社会化建设,这不仅仅限于解决建设资金来源,更重要的是个体在与社会互动中自我提升。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这种良性互动中,其民更具归属感、自豪感。
县志《风俗志》谓,“暨俗联姻谓之接亲”,“婚必择门第”。许多人想当然以为强调门当户对,而编纂者却认为富贵子弟之堕落,“非必运祚衰,良由贻谋浅也”,所以,“择德以谐”才是高明之举。
读山水志至此,我关注了墓志提及的婚配。如枫溪出西埂津龙桥,经峙堂山,有陈翰英墓。据其墓志,翰英者,枫桥陈氏十世祖,是前文提到的陈奫之孙。其“娶骆氏,讳懿简,旌士溪园先生孙女也”。而陈洪绶之祖性学所撰骆问礼墓志正好讲到,溪园公五传至问礼。溪园公即景泰《诸暨县志》纂修者,“好学敦义,受敕褒旌……家声始振”。
如果单说这个,查家谱会更方便。我更想说的是几个大家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孝感山水绕柴爬岭(今仍其名),有东溪先生骆卫城墓,余坤为撰《墓表》。余氏从高湖迁来枫桥,颇有文名。余坤,道光间进士,当时县令杨丹山赏其文曰:“此韩潮苏海也。”(见县志余坤本传)东溪先生是个特立独行之人,“遇不可意者,一言龃龉,裂眦起”,唯与余坤“每谈竟日不可厌”,去世前,还与余氏谈《檀工》、曾子《易箦篇》。
下宣水所经黄罗山,有诗人郭毓墓。其《墓表》曰,绍兴卧龙山麓有祀贺知章等“诗巢六君子”之室,能得配享的,也不简单,郭店人郭毓即在其列。而郭诗人为枫桥陈芝图等三人“评定其诗而合梓之,于是越中三子之名彻海内”。
陈翰英之父南斋先生,其墓志铭谓“少而颖悟,读书过目成诵”,他有个叔父叫陈玑,“时(明)宣宗留意文学,命引见进士百人,选二十人亲试用人何以得其才,论授庶吉士,玑名第四”(见县志陈玑本传),而“先生名与之齐”。叔侄俩“同游学泉溪陈彦平,而才艺相高,时称二陈”。又提到一位人物——王钰,县志本传谓“永乐壬辰进士,以第三人及第”,探花哎!宣德年间修《两朝实录》,“书成,以疾归”。再起,任江西提学佥事,是大名鼎鼎的杨士奇推荐的。南斋先生《墓志铭》曰,王钰“望重当世,不轻许可,独称二陈为不可及”。
说到王钰,不妨再说说他的曾祖王艮。县志本传载,“挟其所为文登大老之门”,得到了赵孟頫等多位前辈之赏识。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听说小老乡王冕其人,“特重之,登堂拜其母”(见县志王冕本传)。
王冕,大家都不陌生。山水志谓,栎溪(今栎江)经桥亭,东流北折,沿郝山,“元王冕七世祖文焕舍小溪山宅为寺,子孙散处。冕曾祖迁居郝山,则郝山为冕生长故里也”。他在绍兴师从安阳韩性时,有个同门兼同乡——陈策,是枫桥陈氏六世祖,“绍兴路总管泰不华荐为稽山书院山长”,拒受张士诚伪官,不屈遇害。
与栎溪相关的,还有马塘水,所出马塘山,“有元孝子楼升墓”,杨维桢为作墓铭,此处不论。杨氏祖上有杨文修者,“生性纯固笃孝,钟于至情,乡人不名其名”,叫什么呢?佛子。“晦庵朱子(即朱熹)尝以常平使者道枫桥,闻佛子名,延与谈名理及医学、天文,地理之书”,这个地方就是紫阳精舍。我在《宅埠陈氏家谱》读到时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的杨维桢所著《陈氏世谱序》,有“吾邦大族所谓世德之美者,则枫川陈氏为右称也”之句。
王冕、杨维桢、陈洪绶,这是书画史上的三座丰碑,论述已浩如烟海。但在枫桥区区之地,从元末到明末这个时间段里,三者横空出世,并非偶然。山水志旨不在此,却多少揭示了枫桥几个大家族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化交流。
(监制 陈惠 策划 周楷华 特约撰稿人 陈仲明 编辑 朱银燕 制图 朱梦琳)

 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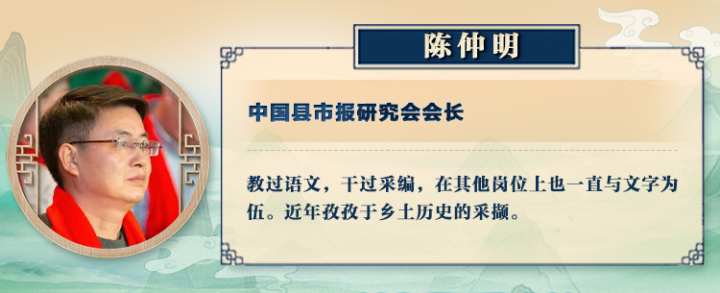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