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未在国内生活过、如今已54岁的陈家明来说,近日全职回国,加入浙江大学是个“疯狂”的决定。他把自己的选择比作旧时的“盲婚哑嫁”,“我还不了解‘婆家’什么样,就‘嫁’过来了。”
看似冲动的背后,是他萦绕已久的那个心愿——回到祖国,培养人才。近年来国内科研环境的改善,让他意识到,“好时机来了”“要趁着有精力,去开辟一番新的事业”。
关于科研
陈家明教授:细胞死亡可分为两种模式:调节性细胞死亡(RCD)和意外细胞死亡(ACD)。具有代表性的 RCD 是细胞凋亡(apoptosis),细胞凋亡是指为维持内环境稳定,由基因控制的细胞自主的有序的死亡,相反,非生理刺激,如物理、机械和化学应力等外界因素诱导的被动和非程序性的坏死(necrosis)是ACD的代表。
我的研究兴趣专注于细胞死亡、炎症和免疫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时,克隆了细胞周期抑制剂INK4d-p19(Mol cell Biol 1995);作为NIH的博士后研究员,发现TNF受体存在并作为预组装的三聚体在与配体结合时发生构象变化(Science 2000),这一发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TNF受体在接受配体诱导后发生三聚化并传递信号的认识。自2002年成立研究小组以来,工作主要集中在阐述一种炎性细胞死亡形式——细胞坏死性凋亡(necroptosis),并于2009年,确定了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3(RIPK3)作为necroptosis的调节因子(Cell 2009),与同期其他实验室共同开创了细胞坏死性凋亡研究领域的新方向。
Q:您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让您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陈家明教授:我很爱看体育比赛,科研和体育有共通之处,那就是永远不要害怕失败。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体操运动员,他在平衡木上非常怕摔倒,是什么样的结果?一位篮球运动员,他如果因为害怕投不进球,而放弃投球,那又会怎样?做科学也是如此,如果因为害怕失败,缺少勇气,就停止行动,不去冒险,那永远不会超越自己获得成功。
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读博士时,有一组实验前后一共做了105次,花了大半年的时光。重复性的实验、一次次失败,我找不到动力继续坚持了,非常沮丧。就在那时,电视中正在播放张德培的比赛,我看他虽然身体素质和美国人、欧洲人相差很大,但是他每次都是全力以赴跑向那个球,用力打回去。我受到了鼓舞,当然在105次实验时,我成功了。所以,不要轻言放弃。
陈家明教授:基于之前的研究积累,团队正致力研发通过调控vIRD和RIPK3功能,来制作更优良的流感、新冠和肿瘤疫苗。
在美国的这些年,有过失败,有过成功,做出了一点成绩。在这次跨越太平洋的回归中,我有自己的使命,利用自己的国际化背景,架起一座良渚实验室与国际科学交流的桥梁。
我认为科学是要有交流的,中国与世界的科学交流要做得更好,让学生们具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同时,我也会尽力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做好引荐服务。
Q:作为一名资深科研工作者,您想要和年轻人分享些什么?
陈家明教授:如果让我从自己的求学经历中总结经验,那就是自主学习,不等不靠。作业做得漂亮、分数考得高当然是好事,但学习的终极评判标准应该是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已经达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程度。
我也想对我团队的年轻人说几句,你应该聆听和思考长者们的经验之谈,但是并不一定要按他们说的做。没错,我是在科研上、生活上更有经验一些,但这不代表我说的都是对的。在我看来,要有独立判断、挑战成见的能力。科学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就是因为总有一群人在深入思考、挑战现状、开创未来。如果我的学生是这样的人,我会非常开心,那是我的荣耀。
陈家明: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
细胞死亡和免疫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本科以院校第一名的成绩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后任杜克大学教授、免疫系副主任。在细胞坏死性凋亡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发表论文累计引用2万多次。

 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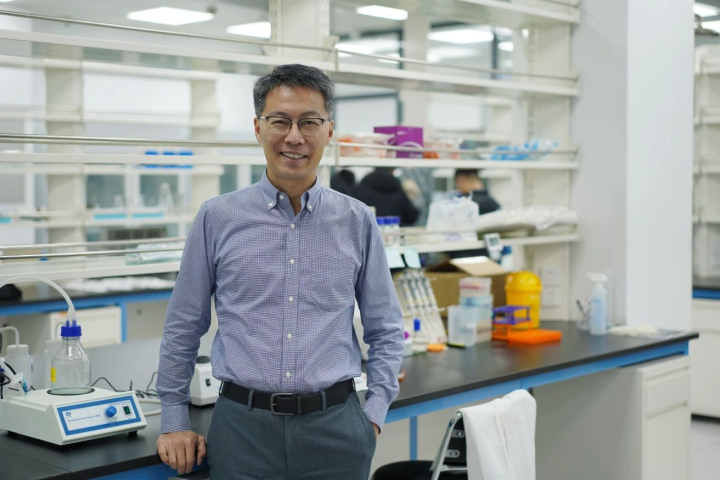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