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物种背后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员:他们如何揭秘“自然密码”?
近日,杭州原乡野地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调查员、湖州市德清县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项目组都在野外调查中发现一种鲤形目鲤科鱲属的鱼类新物种,被命名为“苕溪鱲(liè)”。
随着新物种冲上热搜,背后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员也引发网友的好奇。这是一份怎么样的工作?新物种如何被发现认定?他们为什么会从事这份听起来有点冷门的工作?潮新闻记者采访了数位相关从业人,聆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以“鸟”为名 一眼就能辨别动物种类
“鸥类是我最喜欢的鸟类类群之一,它们很聪明、行为多样而复杂,观察它们非常有趣。所以我以此为名。”王翠的微信名是“小鸥”,这也是她在“鸟圈”的花名。身份上,她是原乡一名全职生物多样性调查员,作为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硕士,毕业后就开始从事这份工作。
不少全职或兼职调查员都取了相关的“花名”
王翠告诉潮新闻记者,在自然观察圈子里,很多人都会给自己起一个“自然名”,可能是一颗星、一种植物、一种自然现象等等,以这种方式表明大家是“同好”,抛开工作、学业、年龄等方面带来的不同,可以更平等自由开放地在大自然里沟通交流。
王翠几乎所有的工作和生活都围绕着鸟类展开,她说自己生活的主线就是跟着鸟跑,哪里有鸟就去哪里。鸟类的调查,通常一年四季都在进行。冬天到来的冬候鸟、夏天待着的夏候鸟,还有春秋两季迁徙过境的鸟类,调查员都不能缺席。这几天,王翠最近常去的调查点是杭州余杭北湖草荡和萧山寺坞岭,探访越冬的鹀类、雁鸭类。
“北湖草荡是湿地,芦苇、灌丛、树林、水塘都有,比较多样。像我们这样有经验的调查人员,走一个来回,大概就能知道鸟类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再结合鸣声,就比较容易找到它们的位置。”王翠告诉潮新闻记者,生物多样性调查的重要一环是设置“样线”。以北湖草荡为例,8条样线覆盖各种生境类型,每条约1至1.5千米长,徒步通常在30分钟至一小时之间。鸟类迁徙季节每月两次,夏季冬季每月一次,一组调查人员少则2人多则5人,带着望远镜、相机等设备观察记录沿途遇到的鸟类。
常见的鸟类,调查员一见便知。对王翠来说,最兴奋就是见到陌生“面孔”,这个时候她和同伴会立刻兴奋起来,赶紧用相机拍下影像,用录音软件录下鸣声,再回去通过对照图片、鸟叫鸣声库进行比对,来确定它的身份。
作息时间跟着种群走
“不同的调查人员很难凑到一起吃饭,我们常说同在杭州,大家也会有时差。”杭州原乡生态保护和研究中心创始人陈奕宁向潮新闻记者介绍,生物多样性调查的类别非常多,除了大家较为熟悉的包括兽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鱼类、植物、昆虫、真菌等。调查员的日常,分为外业和内业。外业,就是在野外的工作,内业则是指对调查进行文献整理、分析等。
外业的时间,自然要跟着调查对象走。“追鸟”的时间,一般选在清晨,即日出后2-3小时。“因为清晨的时候,鸟类是最活跃的,一旦太阳出来,天热了,小鸟就休息了,想要观察记录到它们就很难。”王翠表示,每当到了调查的前几天,自己会自动调整到“鸟类作息时间”,让自己在清晨活跃起来。一般野外调查会进行一个上午,下午就回到办公室进行数据、照片、文字的整理。
不同于习惯早起的“追鸟人”,两栖爬行类调查人员、昆虫类调查人员则可能是个“夜猫子”,习惯于昼夜颠倒。而鱼类调查,则需要“白加黑”。“天黑时下水比较危险,白天需要进行‘踩点’,或者设置陷阱,以便在确保调查人员安全的基础上,准确捕捉到那些晚上游到岸边,或者在水流平缓地方休息的鱼类。”
多位调查人员告诉潮新闻记者,新物种的发现,始于“颜值”。
发现黑腰滨鹬时,王翠和观鸟“同好”们抓紧摄影。
王翠曾在去年发现中国鸟类新记录黑腰滨鹬。据她回忆,当时观鸟团正在浙江龙岗观测鸻鹬,在小滨鹬、半蹼鹬、红腹滨鹬、大滨鹬、阔嘴鹬等近30种鸻鹬之外,还有一只长得有些相似三趾滨鹬,但喙很细长,脖子也比较斑驳的物种,“从外表上看还是有所区别”。
陈奕宁表示,新物种的初步判定主要是通过外表,要想确认,还需要进行DNA的比对分析。在确定基因和外形都有现有物种有所区别之后,需要写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发表了之后,它就会被正式接受,认定为一个新物种。
什么样的人适合这项工作?
陈奕宁曾留学英国学习生物多样性与保护,之前也是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调查员。他表示,生物多样性调查员,是一份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同时也需要对调查领域的热爱。
首先,这份工作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野外经验,以便寻觅调查对象的踪迹。“有些动物很难找得到甚至看到,我们寻找的过程有点像‘狩猎’早期的步骤。我们需要判断它可能在哪些特定的地方出现,根据它留下的痕迹来寻找。”陈奕宁也表示,红外相机也是很重要的助力。
第二是执着,为了调查,要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完全追随调查对象的作息,需要绝对的责任心。
最后,是热爱赢万难。陈奕宁觉得,价值观是要紧事。如果原本就热爱自然,能够从和植物、动物的相处中获得乐趣,甚至人生的信念就是“发现新物种”,那在这份工作中就能得到更多的自我满足。
专业背景在陈奕宁看来倒不是必要条件。他向潮新闻记者提起自己的老朋友周佳俊。“他虽不是专业出身,但一直是鱼类爱好者,捞了十几年的鱼,现在了解程度不亚于专业人士。”
周佳俊给自己取名“黑鱼周”,现在就职于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湿地与野生动植物资源监测处,主要从事淡水鱼类、两栖爬行类与兽类翼手目动物(蝙蝠)的多样性资源调查和保护工作,他也是这次苕溪鱲(liè)发现团队的一员。周佳俊告诉潮新闻记者,自己从小就比较喜欢抓鱼摸虾,对鱼类多样性充满探索求知欲望。虽然没有专业背景,但是在大学毕业后与多家鱼类研究机构的老师有合作,互相交流学习,也一直希望探索到更深的“鱼类世界”。
他的专业知识也切实帮助到了小动物们。今年4月,一头抹香鲸在浙江象山搁浅,周佳俊作为专家前往现场支援。通过微博,他实时更新救援过程,全国上万名网友熬夜追踪。后来,抹香鲸被拖到指定海域,放归大海。在那之后,周佳俊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中,整理数据、去做调查、救助培训。
“我认为好的发现一般还是量变产生质变,常规调查的积累是最重要的。”在周佳俊看来,新物种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人们是否能发现它们的不同而已。自己的乐趣就是能把爱好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发挥一技之长,为累积生物多样性研究基础资料,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做贡献。
“看到鸟就很快乐。”王翠告诉潮新闻记者,把爱好变成了工作,因此自己从工作中能收获很多乐趣,“本身我就喜欢去野外观鸟,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走到野外去,而且能接触到很多更深更专业的知识,比如参与编写《北湖鸟类》《浙江动物志鸟类卷》,学以致用,能够为观鸟的推广、鸟类学研究、公众的爱鸟意识提升等尽一份力,让我觉得自己的价值也有所体现。”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和人生理想,这个行业里,很多人并不在乎高薪,而是更希望自由快乐地工作和亲近大自然。”王翠表示,目前这份工作的收入并不高,也经常被人问及工作的内容和意义,“在工作中,你首先要有一颗亲近自然的心,放下手机、摘下耳机,用眼睛去寻找,用耳朵去聆听,你会发现其实身边的一花一草都很美,城市里也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动物。而新物种的发现,就需要一些好运、耐心和知识的储备。”
“转载请注明出处”

 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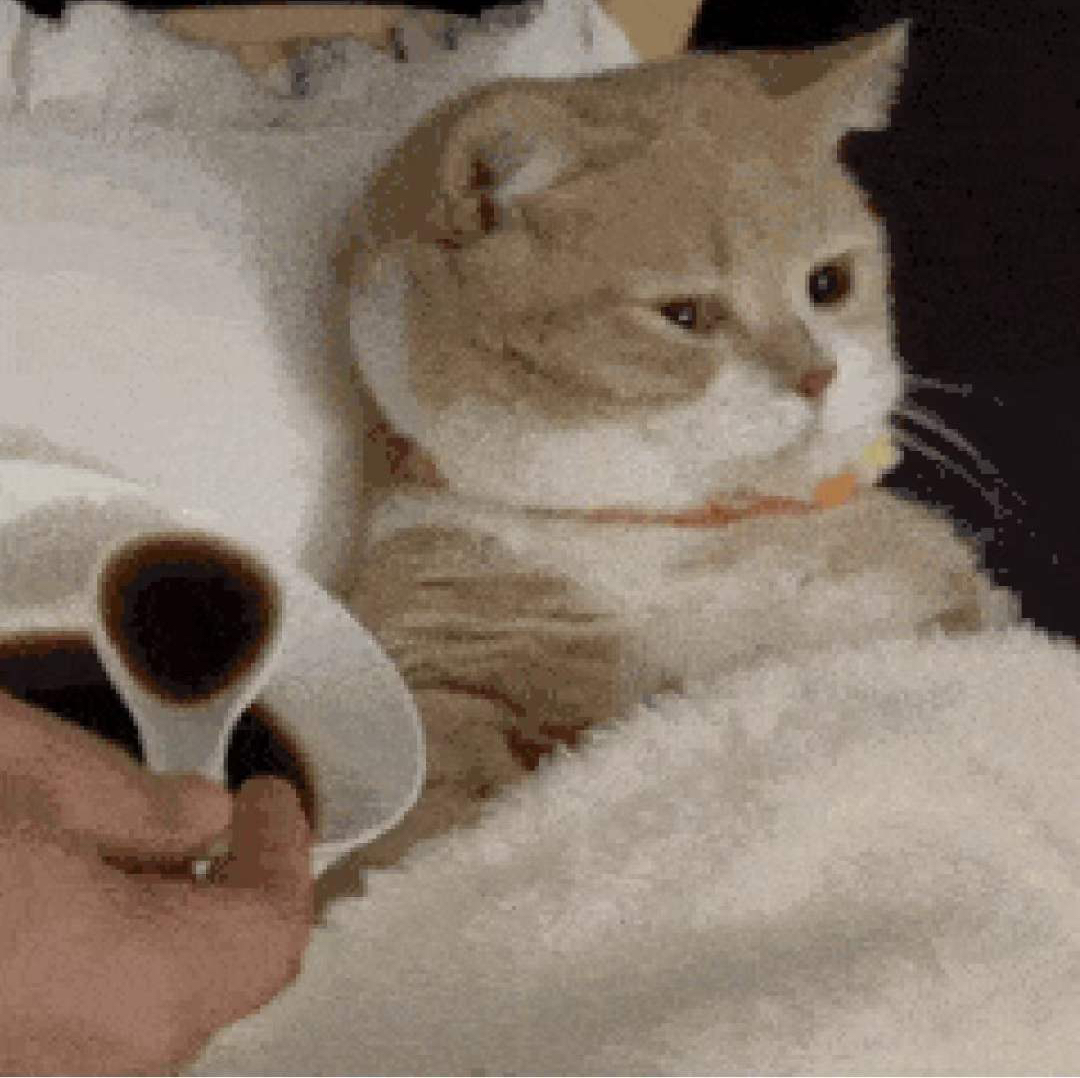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