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童”到“神童”再到“魔童”,哪吒怎样长成
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成功登顶中国电影票房榜、成为中国影史新的单片票房总冠军之后,继续高歌猛进。
毫无疑问,该片在讲述神话故事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一个“神话”!那么,这个让影片都成为了“神话”的哪吒又是怎样长成的呢?
《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含预售及海外)突破100亿 图源:人民日报
哪吒形象的流变
哪吒形象诞生于佛教,传入我国后,一开始主要通过佛经、话本、小说等形式进行传播。元代的《三教搜神大全》将此前的哪吒故事进行了整理。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记》中脚踩风火轮、身披浑天绫、手持乾坤圈和火尖枪的少年神将形象,最为接近我们目前所熟知的哪吒。而这两部小说也是当下影视与动画中哪吒故事改编的主要蓝本。
1927年,顾无为导演的《封神榜之哪吒闹海》成为哪吒故事从文学文本走向电影银幕的发轫之作。1961年,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简称“上美影”)出品的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中,哪吒作为先锋官角色出现,他身披红肚兜,全身雪白,身材浑圆,在战斗时展现三头六臂姿态,最终因大意败于孙悟空。
《哪吒闹海》 图源:央视网
1979年上美影出品的《哪吒闹海》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这部影片极大地丰富了哪吒出生和成长的细节,也将《封神演义》中哪吒与李靖的矛盾,深化为哪吒与政治强权、封建孝道之间的矛盾。哪吒坚守心中正义,不畏强权与伦理桎梏,成就了无惧无畏的少年英雄形象,也让影片充分绽放了英雄主义的浪漫之花。哪吒在暴风雨中横剑自刎,“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悲怆场面令人唏嘘,这是我国动画片中首次对封建孝道进行批判性思考。
2003年,我国第一部大型动画连续剧《哪吒传奇》播出。由于受众定位为儿童,这一版本的哪吒形象基本延续上美影对哪吒的外观设定:大眼、圆脸、扎两只冲天髻、光脚丫踏风火轮,同时消解了原来京剧脸谱的造型特色,使用更加圆润的线条,增添童趣元素,以贴近儿童心理。因为是大型连续剧,需要更宏大的世界观与多样化的人物关系来支撑叙事,于是,《哪吒传奇》将哪吒的成长置于殷商与西岐、女娲与石矶的矛盾之中,总体的改编基调趋于温情,哪吒在一次次冒险中成为了心中有大义的伐纣英雄。
《哪吒传奇》 图源:央视网
2019年,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横空出世,颠覆性的“魔童”视效让观众感到震惊。与以往可爱、俊秀的哪吒形象不同,“魔童”版哪吒有着大大的黑眼圈、玉米粒似的大板牙,走路时双手插兜,一副桀骜不驯的厌世形象。加上性格顽劣、力大无穷,他稍不小心就会“拆家”或者“误伤无辜”。而这版哪吒的外观和性格不仅符合“魔丸”设定,也破除了以往国产动画中“正派一定美、反派一定丑”的刻板印象。
其实,哪吒神态中的厌世感并非没有理由,他生来是魔,被百姓所畏惧,由于父母公务繁忙,他没有同龄的朋友,时常感到孤独。在电影的开篇,哪吒的心愿也不过是有人愿意陪自己踢毽子。从心理上看,“魔童”哪吒更接近一个孤独的成年人,在观影时更容易打动有一定阅历的成年观众。他的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既是对传统哪吒精神的继承,也是为普遍具有自卑、沮丧情绪的现代人注射的一针强心剂。
《哪吒之魔童降世》电影海报 图源:人民日报
现代性“改写”造就时代共鸣
“魔童”哪吒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国人对哪吒传说具有熟悉和亲近感;更重要的是,影片对传统神话进行了现代性的“改写”,角色塑造、画面特效、叙事文本等方面都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经验,从而造就出了属于当今时代的“新哪吒”。正因为如此,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但破除了“续作不如前作”的“魔咒”,还通过饱满的角色塑造,贡献了多个角色的高光时刻,让影片的口碑持续发酵。
哪吒对成仙的态度贯穿了影片的整体叙事。从“当神仙真好”的感叹,到“小爷是魔,那又如何”的洒脱转变,哪吒自我认同的完成正是对前作“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呼应,精神内核带来的情感冲击彻底消解了观众对哪吒“丑萌”形象的质疑。
另外,申公豹、敖光、石矶、土拨鼠妖等一众配角在网络上的热度也很高。这是因为影片擅长以现代幽默来解构神话传说,为角色注入普适性的情感内核,激发观众的情感投射。观众能在申公豹身上看见人性的复杂与立体,在石矶那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获得拒绝“内耗”的鼓舞,还能从“飞天猪”雕刻肉身的剧情中,共情“打工人”面对甲方频繁更换要求时无奈的心情。
《哪吒之魔童闹海》电影海报 图源:人民日报
如果说深刻的情感内核是“改写”过程中直击人心的秘诀,那么,通过“改写”所突出的“反差”“反转”则为影片带来更加强烈的戏剧张力。从哪吒、申公豹、石矶等角色中,观众都能直接地感受到他们外观与性格的“反差”,感到诧异或好奇。“反转”则作为连接观众情感的扭结,隐匿于叙事段落中,将观众的观影过程演变为解谜的过程。谜团揭开时带来瞬时的震惊效果,也因此延展为对“命运与选择”“身份与偏见”等命题的深度思考。
由上可见,哪吒形象从文学走向影视、动画的过程中,经历了从“佛童”到“神童”再到“魔童”的演变。他的成长之路似乎有点出人意料,但仔细一想,这样的成长历程不正显示了哪吒形象的多面性、复杂性吗?而性格的多面、复杂不正是成功的艺术形象塑造的要求和追求吗?也可以说我们现在见到的哪吒走下了神坛,走进了普通人中,跟观众没有了距离,普通观众都可以跟他共情、共鸣。
到此,哪吒便长成为一个被称之为“魔”却更接近“神”的“人”;这一成长叙事完成了对东方神话体系的现代性改写,彰显出真实人性的多维面向,又正因为如此——因为把神写成了人,反而成就了电影(作品)的票房“神话”和艺术“神话”。市场与口碑双丰收的“魔童”,或许会让更多影视、动画创作者意识到:任何试图重构神话体系的努力,都必须以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为前提,所以,要想创造“神”,先得写好“人”;只有让观众与角色共情、共鸣,才能有艺术与市场的共生、共赢。
作者介绍:
盘剑: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影视与动漫游戏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姚悦: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转载请注明出处”

 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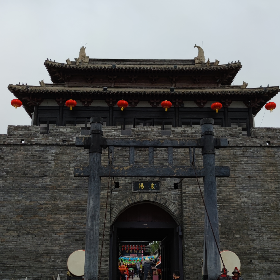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502007539号